![]()
我生于1947年10月10日,农历丁亥年的8月26日,这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当此时,正是国共内战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运筹帷幄与蒋介石斗智斗勇,一年后的几场战略决战彻底摧毁了蒋的政权,全国上下,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在读小学时,老师们就经常说:“你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是那个特定年代打着时代烙印的教育口号,我虽然生在旧社会,却是在襁褓中度过了旧社会的俩年,当然对它不存在任何记忆,因此,今日所忆及的,全是“长在红旗下”的点点滴滴。
我的出生十分贫寒,父母均为二婚。父亲的原籍是本县樊家夭乡善友喇嘛村,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三道营乡水泉村人董氏,与我父亲结婚后育有一子,婚后数年患病身亡,不到一岁的儿子也紧接着夭折。我从后来父亲讲述此事时淡然的语气中感到,旧社会如我父亲一样的穷苦人,亲人的亡故似乎并不比贫穷和饥饿更让人痛苦和绝望,更何况他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母亲的亡故和兄嫂的冷遇,青年时代又接二连三遭遇了妻子、父亲、幼子的亡故,苦难的日子早就磨砺出他性格中的淡然和木讷,所以死亡于他而言,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悲恸。死的已死,活着的还要活下去,家徒四壁的父亲孑然一身后便四处辗转给人打工扛活,甚至揽长工糊口,漂泊无依,居无定所。四五年后,父亲与我守寡的母亲成婚,才终于定居在了舍必崖乡的下布袋沟村。我母亲是上布袋沟人,十六岁时做了下布袋沟马家的媳妇,二十四岁时前夫马三罗不幸病逝,一个年轻的农村寡妇拖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挣扎了几年之后,难以生存,后来经人撮合,与我在当地揽长工的父亲重组了一个残破简陋的人家。父亲孑然一身,母亲好歹有个居所,所以当时看来,父亲是入赘。后来他们相濡以沫四十余年,度过了苦难的一生。
母亲和父亲成婚后,又育有三子一女,我是老二,我还有一兄一弟一妹,加上俩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我们兄弟姊妹共6人。这样一大家人,全靠我那仅会劳动而没有任何技艺的父亲来供养,并给我俩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娶妻成家,其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穷得缺衣少食、捉襟见肘。每年青黄不接之际,总要饿几天肚子,劳动回来的父亲曾经饿得一头栽倒在大门口的粪池子里,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得。16岁之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冬天从来没有御寒的袜子,鞋子也是母亲补了又补、父亲钉了又钉,那种套在脚上沉重、冰凉、坚硬、硌脚的感觉,我至今也还记得。
因为家穷,我念书较晚,十虚岁时才上一年级,是在临村东营子上的,东营子村离我们村约二里地远,是周方围比较大的一个村庄,约有七八百口人。东营子小学是一所一至四年级的公办初级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岱州窑村的胡维景,他尽管学历不甚高,却是一个在周边村乡很有名气、也很受人尊敬的人。这所学校于1961年升级为高级小学,增加了五到六年级,我就是于1962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我虽然入了学,却什么也不懂,也不想懂。还记得当时的一、三年级是复式班,我念一年级。老师前半节课给一年级讲课,后半节再给三年级讲,给三年级讲课的期间,会给一年级布置作业让我们做,我是从来不做作业的,不想做,也不会做,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为了不让老师批评,我就假装削铅笔,一直削到下课,如此伎俩,反复使用。
在东营子小学糊里糊涂念完一年级,我又折回了本村布袋沟念二年级,因为布袋沟村也从别村雇回了老师。我还记得雇回的第一个老师是伍全红老师,然后是刘来老师,他们都是离我村五六公里之外的西厂圪洞人。教室是大户人家的闲房,课桌一律是自备的炕桌,这样就不用板凳也能念书,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学习语文算术,气氛很像旧社会的私塾。时至今日,我的那张炕桌还存放在我老家的老房子里,那张带着抽屉的四方小桌子,是我父亲用十斤猪肉换的,它陪伴着我们姓王的三兄弟度过了人生中的启蒙。
![]()
我的课桌
我在布袋沟念到四年级,又接着去东营子继续读高小。进入高小以后,我的学习竟然突飞猛进了起来,尤其是语文和写作,每到作文讲评时,我的文章几乎次次都是范文,当时教我语文的是舍必崖乡的侯珍老师,他是公立教师,他对我的不吝赞赏和高度重视,使我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我学习的自信。
其实这种状况的转变,与我读书较多有很大关系。
记得前几年莫言在斯德歌尔摩领奖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唯其讲故事,才成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说起故事,我是有颇多感慨的。我当然不能和莫言相比,但启蒙之初的我,却是个爱听故事的人,也唯其听故事,才把我引进了书籍的殿堂。
小时候,我们村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总有几户人家聚起一屋子的人,由一些看过书的人正襟危坐,给村民们讲故事听,人们把这种活动叫做"叨书",我也追着听。叨书的内容大多是武侠一类,像《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呼延庆打擂》《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还有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有“三言”“二拍”。这些书,都由叨书的人整本整本地讲过,他们用绘声绘色的土话把书中情节分享给没有看过书的人。有几个人讲得还真好,把书里那些英雄人物、才子佳人、平民百姓的行为讲得如在眼前,当时那种听书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看戏。由于听书的人多,基本全是大人,我年龄小,总是挤进去听,人家就很不欢迎。后来我就不去听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看书,我要从书中获取更多、更精彩的东西。
我记得我看过的第一部书是《水浒传》,这是我在舍必崖读高小的三哥给我买的,是解放后出版的被清代的金圣叹腰斩点评的71回本。《水浒传》看完后,我三哥也再没有余钱去买别的书,但我已经对书有了更加强烈的渴求。
命中注定我会与书结缘,我少年时期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遇见了我的同学陈新元,陈新元是陈玿的儿子,小我一岁,性格很好,人也聪明。其父陈玿,曾在傅作义领导下的华北剿共总部政工处当过中校秘书,还在临解放前当过和林县的县长,后来随董其武参加内蒙9.19起义,和林一中建校后还当过老师,再后来被划为右派,不久病逝。陈家是书香世家,他们家的藏书很多很多,因为我与陈新元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少年时期所看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起先借的是《三国演义》,是毛宗岗点评的版本,线装书,由于当时我追求的是故事情节,毛的点评基本没有看,后来有了阅读需求很想看,可惜书已经还给人家了。看完《三国演义》后,就接着借了《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聊斋志异》看得时间最长,当时我13岁,由于全是文言,要看懂,就须细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是靠着一本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词典一路走下来的,攻克完这本书后,自我感觉收获颇多,写文章也变得顺手了起来。
除了陈新元,我还有另外俩个来书渠道:一个是我外祖父的兄弟李世江,一个是本村的牛培珍。
我外祖父据说也是个读书人,他去世早,我没有见过,外祖父的弟弟李世江,我叫“二姥爷”,此人四书五经全读过,还是个中医大夫。巧的是,外祖父兄弟二人的子嗣们全都不爱书,因此他们的存书后来基本上全部被我继承,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俩部书是《幼学须知》和《古文释义》。尤其是《古文释义》,其中尽是名家名篇,它和《古文观止》的文章大同小异,有些甚至比古文观止囊括的内容都要多,有些名篇我都能把它们背下来,比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介子推不言禄》,还有其中的《苛政猛于虎》《归去来兮辞》《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直到现在其中经典之句段还时常萦回于我脑海。还有一部朱熹集注的《诗经》,是木版印刷的书,这些书我都如获至宝,不停地诵读,尽管不十分懂,但读得多了,也如古人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另有一个来书的渠道,是牛培珍给我提供的,牛培珍小名叫牛兰田,他也是我的同学,他的父亲牛永富也是个读书人,在旧社会还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后来也是随董其武起义的一员。牛兰田给我提供了两部很有价值的书,一套是白话四书,这套书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并把它们全部抄录了下来,我的古文突飞猛进,与抄录这部书有很大关系;还有一部是《三苏文萃》,是苏东坡父子三人的论文合集,其中有两篇我崇拜至极,即苏洵攻击王安石的《辨奸论》和苏轼歌颂张良的《留侯论》,这两篇文章的语言与所表达的思想对我影响甚深。
现在想来,我学习古文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起初是为了看一些文言小说,追求热闹的故事情节,后来对一些文学评论我也爱好了起来。比如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尽管它是白话写成的,我一开始好歹也是看不进去,直到看了胡适乃至许多红学家的各种介绍及评论,我才逐渐对它有了兴趣。我后来常想,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书象《红楼梦》那样引起广泛的评论,甚至还由此衍生出一个“红学家”的群体。其评论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甚至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对它赞不绝口,这就逼得你硬着头皮也要把该书读下去,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读书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也开阔了我的视野。进入高小以后,伴随着我对古籍的阅读,现代小说也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部现代小说是反映抗战的《烈火金刚》,接着我又读了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巴金的《家》《春》《秋》等,矛盾的《子夜》,郭沫若的《洪波曲》以及周而复的《上海的早城》等,农村体裁的,我读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 在桑乾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至于后来出版的一些小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书,更是反复读了许多遍,而且对我的影响更深。另外,外国小说我也读过一点,如《日日夜夜》,《海鸥》,但印象都不深,而印象最深刻的,是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书中的主人公保尔当作圣人一样的崇拜。
读书越来越多,视野也变得越来越宽,思维也越来越缜密,表达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真正体验到了"开卷有益"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精髓。
我是1962年从东营子小学毕业的,那年6月,我在董家营公社所在地参加了小升初考试,我们班有8位同学考入了和林一中,即东营子的冯聪 、秦国栋、秦万宝、秦锁恒和孙秀芬,布袋沟的我和刘高万,麻黄圪洞的张士英。
我上学不多,但教我的老师很多,我至今印象很深的有三人,即舍必崖乡土不灿的侯珍,巧什营乡大新营村的兰春茂,还有董家营乡麻黄圪洞的王建直。他们三人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都是值得称道的。我念书时,他们对我都很关注,但每年给我的操行评语中都有“个性太强”这样的评价,我在当时还不甚理解,后来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我才渐渐理解了这一评价的真谛。我一生的各种不得志、各种吃亏,恰是因为这一性格导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性格,我这一生,也基本都遵从自己的内心活着,使我自己成了一个“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无愧于自己本性的“匹夫”。
被中学录取的那一年,我的三哥王修也考入了托县高中,家里太穷了,我父亲决定只供一个,我三哥也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又比我高出三个年级,所以我只好辍学,三哥继续读书,三年后他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
辍学后我就开始劳动,每天和生产队的队员们一块上工, 一块干活。由于六年来养成了习惯,所以尽管不念书了,晚上回家我仍然继续看书学习,我常常把一些需要记住的东西写在胳膊上,或劳动工具上,如锹把和锄把上,我向来记性好,不用专门去背诵,这样一天下来,也能记住不少东西。缺点就是字写得很潦草,很不规范,我一辈子都写不好字,大概与这种习惯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
回忆录手稿
我们的村子不大,却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村子,由于我看的书多,开言吐语自然带着一点文化气息,这赢得了一些父老乡亲们的看好与重视,他们纷纷向我父亲提出建议,即使砸锅卖铁也应该供这孩子去读书,否则将是一辈子的遗憾。记得当时和林一中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父亲果然被人们说动了,他向在公社当大夫的我舅舅借了20元钱,下决心准备送我去一中读书,我高兴地向我的俩姨表哥贺兵在打听,问他迟去一个月,学校还收不收,贺兵在回答我说:"收,肯定收!",他还说,学校公布了新生的名单,他看到我被分配到了27班。他的话更给了我无限的期待和向往。
然而,大概是生活想和我开个小小的玩笑,我本来满心欢喜地准备去一中念书了,收拾行李时才想到,连一床铺的褥子也没有,这个奢侈的东西,我们全家谁也没有,盖的被子也是破烂不堪的旧棉絮烂布子补衲出来的。此情此景,我父亲只能安慰我说,人家刘二那么有钱,还不让儿子去念书,像咱们这种穷人家哪能供起俩个念书人。
我念书的梦想终于彻底破灭了!和林一中27班,从此在我的心里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名字。
记得当时布袋沟在一中读书的人,有南头的张团凤,刘枝莲,陈彩萍(陈新元的姐姐),北头的李文善,贺兵在和刘连万。每到开学时,我看到他们相跟上步行去40华里外的一中求学,他们那有说有笑的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反观我自己,却和村里的社员们在一起扛锄头送大粪,我当时心里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受滋味,说实话,我并不鄙视劳动,但我更爱念书。刘高万也没有去念书,那是其父刘二故意没有让他去,他家的光景在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刘二曾和我父亲讲,说娃娃们念成书以后就会离开家,见面就很难了。由于刘二的些微影响,加之我家实在是穷得无力承担,这就决定了我的求学之路只能止于小学六年级了。
我彻底与学校无缘了,只能老老实实待在生产队里劳动。当时的国家政策是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我家是下中农,但由于我村的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与我们家里人的关系不十分好,所以即便再穷,当然也得不到关注。当时我们村的小学要用俩个民办教师,大多数社员都推荐我去,但队里的干部不用我,而是用了另外俩个人,一个是没有考上高中回乡劳动的李文善,这个当然无可非议,因为李文善毕竟是在和林念过初中的人。但用的另一个人却是我的小学同学,此人念书时在班里成绩倒数第一,用他的唯一原因是,他是队长的堂弟。
我只能跟随大伙继续我艰苦的劳作,我劳动速度极快,干活却不精细,我经常挤出劳动的时间读书,劳动质量差,就经常被扣工分 。还一度因为我扣工分最多,队里人们给我起了"老扣"的绰号,甚至在老年回乡时,乡亲们还亲切地叫我这个绰号。
1964年,村里的牛茂全当了生产队长,安排我开抽水的柴油机,这在当时也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记得当时我们村正在打一眼大口井,全村的男女劳力足有五六十人,一起在村东边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打井,那时的水位较低,俩米左右就见水了,见水以后要再往深挖,就得不停地往外抽水,以防淹没打井的人们。后来打得深了,井下最底层的人穿着及膝的长筒雨靴也挡不住越来越高的水位。一个叫云雨世的人在下边吆喝我:“老扣,发动机器再往上抽一股股水!”我就发动机器又往上抽,由于水和泥沙混到一起,10马力的柴油机负荷太重,怎么也抽不上来,我就把阀门开到最大。这一开不要紧,直接导致柴油机飞车,滚滚的黑烟上串,凄厉的轰鸣声响彻天空,我吓得不知所措……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噪子:“机器爆炸呀!”,这一喊,把当时在各个台阶上往上运泥沙的人们吓得撂下工具抱头鼠串,直跑到离大井很远的地方才停下。然而最后,机器并没有爆炸,它像一头发疯发累的猛兽一样,燃尽了油,自己偃旗息鼓停了下来。
自此以后我就辞职不干了,我深知自己不懂物理,操作不了机器,也不感兴趣,不是干这个的料。若干年后我从乌海调回和林,我的三哥曾打算让我去邮电局开大车,那时汽车司机也算是十分吃香的职业,但我不爱,坚决不去,说心理话,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那时我真的选择了司机这一职业,或许一些无辜的生命就会死在我笨拙的车技之下了,而和林县的教育系统,也就少了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
命也,运也,我不讲迷信,但是有些事确实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你只能接受和顺应它,然后多做准备,多储备知识,机会来时再努力争取。不然的话,终会被时代淘汰。我始终相信,命运总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
【作者简介】
王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1947年生,中共党员, 1969年参加工作,先后于和林二中、和林一中任教,现已退休。
来源:王利君推荐
编辑推送:【文仙雅阁】微平台~主编小鱼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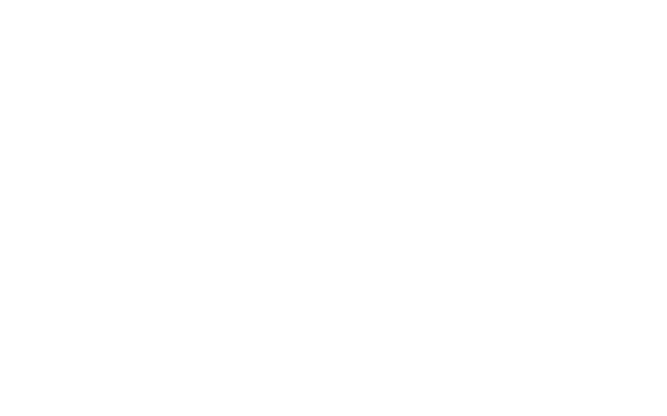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