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愣福来挨打,引起了一场全村的风波。
愣福来躺在炕上,滚来滚去,像一头被捅了一刀没断气的猪一样嚎叫。两只脚乱蹬,把过年时刚换的新芦席蹬成了一堆烂草。硬得像马蹄子黑得像猪蹄子一样的双脚被芦席的尖刺划得鲜血淋淋。他的鼻梁骨被打断了,两只鼻孔像两洞枪眼,不断向外喷着血。他干嚎着,哭着,骂着:“牛金龙,你凭什么打爷?你赔爷的蛋泡子!”
福来妈干枯的脸上布满了斜七倒八的皱纹,泪水顺着皱纹曲里拐弯流淌。
她双手按着儿子诉述着:“福来,你什么时给妈省点心啊!早就说过,不要乱跑,不要瞎说,这不,给自己遭罪呀!”她喃喃了一阵,用袖头擦把泪脸,睁起了布满血丝的眼,又骂起金龙来:“金龙!你个没头的灰人,迟早不得好死,对个愣子也能下这黑手呀!”
福来又嚎起来,双手捂着裤裆:“妈呀,金龙踢烂我的蛋泡子了,好疼呀!”福来妈惊骇地颤抖着双手,问:“福来,和妈说,真的踢伤了?”“妈呀,脱了裤子看呀!疼死我了呀!”福来痛得龇牙咧嘴,翻滚不断。福来妈“噌”拉开儿子裤裆,吓呆了,两颗睾丸肿得像吹起来的猪尿泡,青黑青黑放着光泽。她老人家尖吼了一声,双手捂上脸也嚎起来。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许多男女进了屋。说长的,道短的,叽叽喳喳,像麻雀吵窝,忿忿然斥责牛家人欺负一个愣子。
这时,一位老婆婆站出来,她长着一张锈烂了的犁头似的脸,干枯,瘦黑,找不出两眼的位置,尖嘴,棱鼻,披着一头枯草似的头发。这老婆婆是杨大户的一根旗杆。那年,她儿子杨来喜因调戏牛老栓女儿迎春,让牛家弟兄打拐了腿。为此引起牛杨两家半个月的大战。两家从祖宗到现在,势不两立,从不过话。今天她来到了福来家,气得嘴唇子直打哆嗦,拍着炕皮和福来妈说:“老姐姐,这牛家仗着儿多,欺人也太过了。这事不能让过!”
“老妹子,不看佛面看爷面呀,要没有玉龙的面子,我去和他们拼命!”福来妈也用干瘦的巴掌拍打着炕皮。
“面子算个什么呀,把那东西踢坏,是断根绝户的事!”杨来喜的妈继续煽火。
福来妈摇着头说:“那倒淡事,像我们福来,去哪再找老婆?就算有了老婆,再生一群愣子,还不如不生。唉——说到底是上辈子损了大德,呜——”她伤心地哭了。
“大婶子,不要哭了!”又一个杨家女人虚张声势,尖叫起来,“快救人啊,福来不行了!”
这女人的话把人们惊呆了。福来也趁机装成死相,把人们吓得拥出了屋,不一会儿,满村子都知道了福来要死的消息。福来家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了,多数是杨家人。满院是臭骂牛家的声音。
金龙打坏了福来,急坏了牛老栓,他去找朱阴阳给福来看伤。朱阴阳着实有些为难,他摊开双手无奈地说:“牛大哥,招个神驱个鬼我成,算算命相也凑合,看病的事我可干不了。”
牛老栓却不依不饶,求告道:“朱老弟,求你了,你平时不也常给乡亲看病吗?”
朱阴阳推不过,只好实话实说了:“牛老哥呀,不是我不帮忙。福来虽说是个愣子,但毕竟是马家的人。马家在村里的轻重你也知道,牛马两家原本就不合,今天福来被牛家打成这样,马家人会善罢甘休吗?还有,杨家和牛家也是世仇,
杨家又和马家亲套亲,杨马两家利用这事合起来和牛家干,我能吃倒人家?现在我跟你去给福来看伤,该咋说话?说福来伤重了不利你们牛家,说伤轻了,马家和杨家能让过我吗?”
牛老栓用粗糙的大手拍打着自己的眉骨,心里想也是这么回事。从打自己记事起,村里的牛杨马朱几大姓总是磕磕绊绊,虽然大几十年过来了,总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近几年,各家族之间越来越少了信任和往来,矛盾越来越深了,明显地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是牛朱两家的阵营,一是杨马两家的阵营。虽说从人数和势力上牛朱两家占绝对优势,但杨家没什么文化教养,野蛮粗暴,马家又出了油屁股维持会长,折腾起来也常常叫人挠心。牛朱两家一向友好,朱家为帮牛家也吃过不少苦头,今天就别再麻烦朱阴阳了。牛老栓一边往院外走,一边赶快回家。大儿媳小兰还在山里放羊,得让小龙马上找回来。小兰前几年陪她爹去范家镇看病,认识了一个出名的老中医,让小兰出面去请请。他刚跨出朱阴阳的大门,朱阴阳从屁股后头又追上来,说:“牛大哥,我又想了,那我就去看看福来吧。”
牛老栓不胜感激,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再谢谢朱老弟了!”
玉龙、小龙和玉茭大步流星往村里赶。
玉龙心里好乱。在牛家村,没经过明媒正娶在野外偷情是大逆不道之事。
全村长嘴的都会发出议论和耻笑,臭名声顷刻便会在全村乃至周围村落像瘟疫一般传播开来。自己是个男人,咋都好说,可玉茭怎能忍受那种疾风暴雨似的谴责?他对福来,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论咋说,他是个愣子,金龙不该出手打他,而且打的那么重,听小龙说还有生命危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马家人会不会善罢甘休?杨家人会不会从中挑唆?原本纵横全村的各种家族矛盾都会为此恶化。若是这样,我玉龙可就成全村的罪人了。
玉茭使劲拉着牛缰绳,想让慢悠悠的老牛把步子加快。可老牛并不随心,故意扬着头,“哞——哞——”地叫着往后退。
“小龙,我和玉茭先走,你在后面拉老牛,要不,什么时能回了村?”玉龙把肩上的犁头递在了小龙的肩上。
小龙扛上犁,说:“三哥,玉茭院里挤满了人,都是杨家和马家的人,一齐骂咱们牛家,你一个人去,非把你活吃了不可。”
玉龙沉静地说:“二哥把福来打成那样,谁看了也不公。骂就让人家骂吧,谁让二哥打人家!”
玉茭也说:“不怕,打着我们家的人,与他们有什么相干?”
玉龙摇摇头,说:“玉茭,不是那么个事。他们为你哥出气不是心疼你哥,是想借这个由子为他们马家和杨家出气!你还不知道村里这些恩恩怨怨?”
玉龙和玉茭撒开腿向村里飞跑,把小龙和老牛远远抛在后头。
忽然,玉茭从后拉住了玉龙,然后依在了他怀里说:“玉龙,你怕吗?”
“怕什么!”玉龙反问。
“不怕村里的人笑话?”玉茭的大眼睛盯着玉龙。
“不怕,我是担心你!”玉龙说了真话。
“我更不怕!我哥把咱们的事办砸了,弄大了,其实也不算个坏事,干脆咱们就那样了,谁想说什么就说去!”
玉龙说:“玉茭,自古以来,婚姻大事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们都没这些条件,我爹妈这一关就难通过,还得慢慢说服老人。”
俩人进了村口,便听到熙熙攘攘的吵声。抬头望望,玉茭家院里的人群如一堆蚂蚁。玉龙放慢了脚步,想让玉茭先进院,自己随后。玉茭却扑上来,拉住了玉龙的手,大声说:“怕什么?咱们就故意让他们看看。玉龙也鼓起了勇气,步履更加坚定。他们的行动,明显是做好准备,要和预期而至的流言蜚语挑战和抗争。他俩手拉手,走进了人群扎堆的院子。
院子里,突然发出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接着许多女人都惊叫起来。她们边呼叫,边用双手捂住了脸,有的脸背向了墙壁。玉龙和玉茭的行为竟使她们感到如此的不堪入目。她们似乎看见魔鬼进了院子,在她们感到惊异的同时,院子里的人们就“嗷——嗷——”地齐声叫起来,这是嘲笑,是抗议,也是愤怒和起哄。
玉茭脸涨得像落山的太阳那么红,一扭头,两根辫子拨浪鼓似的摆了几下,道:“嚎你妈的丧?你们不知男女的事情,是从狗屁股里生出来的?”
“呀——呀,玉茭可长本事啦!办下这见不得人的丑事,还张嘴骂人啦!”杨来喜的妈用手指指点着自己那张锈犁头似的脸说,“还懂个羞吗?你把马家的脸丢尽了!”
“我丢了马家的脸,与你杨家有什么相干?我还顶不住你们杨家?死皮赖脸缠人家迎春,腿都让人家打拐啦,那就不羞啦?”
玉茭话音未落,杨来喜拐着一条腿冲过来,巴掌在空中掂了又掂,试着要打玉茭的脸:“你个卖大蒜的婊子,今儿爷爷一个耳光扇上你西天!”
玉茭一步跨在了杨来喜面前,把脸横在他举起的巴掌前激着他说:“打呀,打呀,你不打就是毛驴养的!”
“打这只母狗子!”杨家一个干头小子冲上来,替杨家助威。并首当其冲捅了玉茭一拳。玉茭正要往上扑,玉龙一把拉住了她,把她推到后头,说:“打架的事还轮不着你哩!”他说话的当儿,眼疾手快,两只手同时掳住了杨干头和杨来喜的两根大辫,把两颗脑袋拽到了一块,两只手绕了几绕,两条辫子就被挽成了死结。俩人背对着背,被连在一起,干嚎叫骂,但谁也不能动弹。玉龙对杨来喜讥讽地笑了笑,又转过身用手摸了摸杨干头的脸蛋,说:“打架的事你还没领教够?”
杨来喜的妈像一只不叫的母狗猛地扑了过来,想用头把玉龙撞翻。玉龙把身子一闪,她的头不偏不正撞在了儿子杨来喜的裤裆心,儿子痛叫了一声,骂:“你往哪儿撞?”
玉龙仰头大笑之际,杨来喜飞起一脚,向他裤裆踢去。玉龙早有准备,一只手抓住了杨来喜的妈,顺势搂在自己眼前,挡住了杨来喜的飞脚,那一脚落在了他妈的小肚子上,那婆娘双手一捂肚子,就势坐在地上,妈呀老子地喊着痛。然后就把双手扬上了天,哭喊:“杨家的人死光了,就让牛家人这么欺负呀?”
杨家的人都聚过来,把玉龙和玉茭团团围住。杨家的女人们在后头喊着叫着骂。马家的一些人也凑合在一起,手指雨点般落在玉龙和玉茭的额头上,恶言污语像暴雨一样落下来。
这时玉茭妈双膝跪行着,从人们的腿林中钻进了人围中,披散着银丝乱发,转着圈儿向围攻女儿和玉龙的马家杨家求告:“侄儿男女们,乡里乡亲们,我求你们了,你们可怜可怜我吧,千万不要动手啊……”
一声大喊把人们震惊了,二狗、飞飞和二木匠一伙后生冲进了院里。他们手里都拿着木棒和粪叉,拨开了人群,把玉龙护在中间,和围攻的人对峙起来。
玉茭妈看见打架的阵势越来越玄,里一头外一头地乱磕,用近乎绝望的语调向上苍喊着:“老天爷,你制制他们啊!”
张老先生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不仅年岁高,也是村里文化最高的长者。自从玉茭爹死后,他和玉茭妈就成那种事了,村里人也习以为常,他也常以玉茭和福来的家长自居,出面解决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他就自然成了马家的一员。可他又和牛家朱家关系不错,是个八方都能兼容的人物。加上他给全村娃子当私塾先生,家长都靠他培养出个龙呀虎呀的,都很尊重他。平时他说话很有分量,也能站住地方,家乱也好,村波也好,他一出面就能平息。此时如果他在,事态不致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张老先生哪能闲住啊!他从私塾房出来,路过牛老栓家,牛家大院里也在打架。
事情是二狗的媳妇桃桃引起的。桃桃在村里听说马家杨家联合起来和牛家打架。她和金龙有染,害怕金龙吃亏,就到了牛家大院。金龙正在羊圈旮旯撒尿,还没拉住裤裆,她就凑上去,扒在金龙耳朵上咬话。偏让巧巧从窗口上看见,她从屋里扑出来骂:“你个卖大蒜,没等黑就等不得了?”
桃桃毫不犹豫迎了上去。双方没有任何解释,互相抓住了对方的肩膀,拧过来,扭过去,互相唾骂。巧巧照准桃桃的大奶子用头撞去,桃桃以头相抵,“嘣”地一声,俩人眉头上各起了一个疙瘩。
金龙怕拉了偏架。这两个女人,他谁都不敢招惹,随着俩人扭动和撕拨,他转过来又转过去看。巧巧从后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肚上,骂:“你个王八,也不晓得帮忙?”
金龙捂着肚子向屋里大喊:“迎春,迎春,拉架——拉架——”迎春从屋里跑出来,金龙趁机跑了。
迎春架在俩人中间,想从中分开,可俩人抓得死紧,谁也打不着谁就互相唾起来。迎春的两个脸蛋上沾满了黏稠的带着血的唾沫。
牛老伴提了一只鸡毛掸子,照着巧巧和桃桃的两颗脑袋打起来,东一掸子,西一掸子,你一掸子,她一掸子,立马,鸡毛满天飞舞,掸子马上秃了头。老太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地上大喘气,疯二姨拍着大腿“咯咯咯”地大笑,好像正月十五看红火那么快活。
这当口,张老先生进了牛家大院。他喊骂着,冲上来正要动手拉架,疯二姨一直快活的脸,不知为什么顿时变得愤怒起来,她指着张老先生骂道:“你这个日本判官,奶奶今天把你干头打烂!”她十分凶恶地奔过来,操起墙上挂着的扫帚就向张老先生劈头打下。张老先生赶紧躲开,脚下一闪,把腰扭了,随即跌趴在地上,嘴啃了地,原先嘴里统共有五只前门牙,这回又碰掉了两只,满口鲜血涌出。
他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
小龙拉着老黄牛进了院,见迎春搀着张老先生,妈妈坐在地上乱骂,二嫂和桃桃还在不分胜败地互相揪扯着头发,小龙骂着:“爷让你们好好地打!”随后从牛头上抹下牛缰绳,拦腰把两个女人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谁也不能动弹,他一推,俩人倒在地上,四条腿在空中乱蹬,又是嚎叫又是哭骂,院里一群鸡子早被吓得飞到了屋顶,只留那个走俏的母猪“吱吱吱”地叫着,在院里乱窜……
太阳歪过正中,两处院子的战事才算结束。福来院里,先是福来爬起来出了院,刚才要死要活,现在没事儿了,看见院里这么多人,很热闹,他还咧开黄牙憨笑。他没了事,马家和杨家想借机发挥也就没驴劲儿了。接住是牛老栓和朱阴阳进了院,老栓见双方对阵,冲到阵前,脱下大鞋照着玉龙头上盖去,玉龙趁机拔腿跑了,跑了就了啦,老栓又给乡亲们说了下情的话,加上田地里耕作的乡亲们都逐步回村,打帮的劝说的,人们也就各自散去。
老栓回了自家的时候,院里的战事也已停息。只听见了二儿媳妇在屋里哭,老伴在门口骂,疯二姨哈哈地笑。张老先生满脸血迹,嘴巴肿得像猪嘴一样,光摇头摆手叹气,显得无奈。二狗的媳妇桃桃骑在自家的墙头上,又拍大腿又跳高高,仍在牲口八道臭骂。
牛老栓用力地在院里踮了两腿,再也坚持不住了,手扶墙头,撅起屁股又大咳起来。
![]()
【作者简介】
田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诗人,原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发表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六部,诗词集两部,尚有言论集,文学评论集两部。约七百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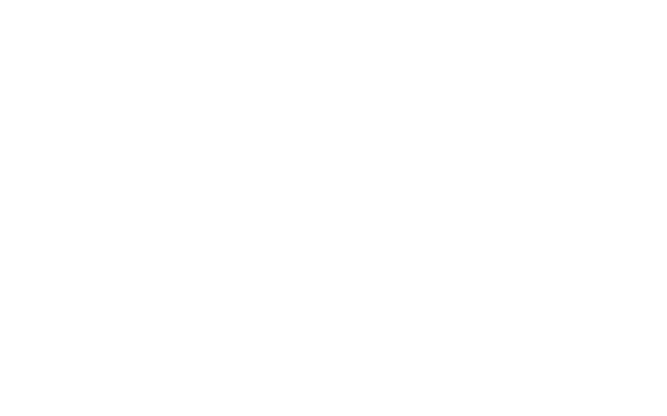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