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雪山下的 YAK
2013年10月24日,在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大环线的徒步中,我们抵达了马南(Manang,3565米)。
这是大环线上一个物资丰富、条件相对舒适的大镇,停留在此的徒步客较多,全队17 个人和5位背夫只能分散在三个客栈住宿。
我们住进的一个有天井带露台的客栈 YAK,建于 1983 年。海拔升高了,房费也由最初的 100 尼币涨到了150 尼币,餐费甚至我们晚餐时必点的啤酒都有了涨幅。
爬上客栈的二楼后,站在楼道的露天回廊上,正好面对着南面的露台,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子——她坐在木桌前,正在专注地读着手中的书。阳光自半空而落,整个露台都罩着一种温暖明亮的氛围。
![]()
露台上迎着风鼓动着的经幡,墙角周围摆放的花盆里盛开着万寿菊和雏菊,甚至经幡边缘的丝丝絮絮,轻轻摇曳着黄色花瓣,还有女子披肩的金色发丝,都在逆光中焕发着奇幻迷人的光泽。而露台背后,是几乎近在咫尺的冰川。
傍晚,大家一起在露台喝着现烧的热茶和啤酒,也才细细端详身旁的雪山。刚嘎普尔纳峰(Ganggapurna,7454米)和东侧相邻的安娜普尔纳Ⅲ峰(7555米),此时在我们面前并肩而立。
而离我们最近的,则是刚嘎普尔纳冰川(Ganggapurna Glacier)铺泻而下的巨大冰舌。冰川堆垒卷积,气势劈空,却凝固如雕塑——在岁月面前我们何其渺小,根本无法领略它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何其幸运,能够一睹它用亿万年的工夫塑造的作品。
![]()
二、弹着吉他唱歌的老捷克
从马南开始,我们暂时离开安娜普尔纳大环线,按原定计划,由西北方向转向西行,用两天时间徒步往返近 5000 米海拔处的世界高湖提利乔克湖(Tilicho Tal)。
景色越加荒凉,雪山在身侧,越发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紧紧攥着你的心,让它有一种莫名的疼。在我们的身畔,安娜普尔纳山系最壮观的一组山结已经开始呈现。
从我们已经熟悉的安娜普尔纳Ⅲ峰,刚嘎普尔纳峰,到作为安娜普尔纳Ⅰ峰卫峰的冰川穹顶峰(Tare Kang 7069 米)和黑岩峰(KhangsarKang 7485 米),这些 7000 米以上的雪山在距我们数十公里的南面一字排列,直耸天穹。
![]()
高山仰止。
有句梵文谚语说:“喜马拉雅山的奇妙,真是妙不可言。如果要想一一描述,那么说一千年也说不完,说一万年也说不清。”
我们无法分辨清每一座雪山每一个峰尖,但一次次停下脚步,面对它们,不正是面对着苍茫的天空和深远的大地吗?不正是面对着亿万年间时光雕琢塑造出的地老天荒和海枯石烂吗?
![]()
去往提力乔克营地(TilichoBaseCamp,4175米)途中,在康萨尔(khangsar 3785米)的客栈,我们遇到了老捷克。他的队友们都前往冰湖高海拔区了,他留在此处,等待他们从冰湖返回后会合。
正是午后休整时间,大家心情都挺好,用半生不熟的单词跟老捷克聊天。牧民哥和水手、高原红从客栈先后买了啤酒,请老捷克一起喝。这些日子以来,大家都有些体力及心力上的疲乏,难得能这么兴奋。这是我们在大环线上喝啤酒最多的一次。
如果不是零红蝶说后面的路有点险,阻止大家再叫啤酒,恐怕我们会一直这么喝下去。后来,他拉过我跟老捷克比比画画地说:“她,很喜欢你的歌,来晚了,你能为她,再唱一首吗?”
老捷克欣然同意,取过吉他,依然微笑着,弹唱起来,曲调十分欢快。他发着很重的卷舌音,眼神慈爱,岁月涂染于他的沧桑,很有种奔放和洒脱,极为符合那歌中的意境。院落直对着雪山,峰顶不时拉起一波雪旗,又转瞬消散。
大家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老捷克也被我们的情绪感染了,于是便坐在阳光下,为我们唱了一支歌,又一支歌。我们便一直围坐在他的身边。
是老捷克和他的歌声,使我们彼此视为故友——此刻的他,像是正开着一辆拉风的老爷车在田野间奔驶,禾木芬芳;又像是,和朋友们坐在池塘边看日落,流光似水。
![]()
三、缓慢上升
10月28日。我们从亚库卡尔卡(Yak Kharka,4060米)出发,在客栈夹峙的村道上,回首还能看到正南方向的安娜普尔纳Ⅲ峰和刚嘎普尔纳峰,雪峰都被浓云笼罩着,山体便更显得深沉肃穆。
午后,我们在陀龙费迪(Thorung Phedi,4560米)客栈陀休整。陀龙山谷开始起风。没想到风势如此强劲,不断卷起山谷中塌方区的浮土,也将一些没有牢牢固定的东西刮得呼啦作响,声音听起来很是瘆人。
在喜马拉雅山区,受地理因素的影响,河谷多数成为气流的通道,当冷热气流交汇,都会在下午阳光强烈、温度最高时产生强劲的风。大风是从山上下沉的冷气流,所以在上山途中,便会顶风而行。
![]()
从陀龙费迪到陀龙高地营地(Thorung High Camp,4905米),其实只有两公里的路程,但这段路的海拔上升近 400 米。往复之字形上升的陡坡,耸立如山门般的兀岭,看起来让人心里就生出怯意。路上遇到的老年徒步团队依然在按照他们统一的步速前进,他们在陡坡的小路上排列整齐,就像一队扛着大木头搬家的小蚂蚁。但这样排着队一步步向前走,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拼合体力、抵御狂风的方式。
看着周围的山形和地貌,虽然知道前面山脚下的路将通往营地,但在三面围墙般的山体逼兀的视觉中,有种坠入世界尽头的沦落感。山风吹得人无法呼吸,寒冷使身体急速地散失着温度,海拔高度压迫产生的错觉使这段路无限延长,还有狂风中飘落树叶般的孤独无助感……
![]()
四、“勺子”
后来,拉仁看似是已经到达营地又返回来接我们了,他从米勒那里接过了我的包,并拉着我往山坡上走。
风似乎已经把我吹透了。冷、恶心、眩晕,加上胃的不适、腿部的疼痛,我觉得自己已经快像一摊烂泥了。拉仁只好搀扶着我,走几步让我靠着他休息片刻,遇到有挡风的石壁,让我坐在下面喘几口气,就这样,一步步往上挪。
在高海拔区域的徒步,雪山带来的震撼和路途对身体的折磨同样强烈并起伏不停。上坡,转弯,再上坡,再转弯……这段路我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快到营地时,远远地就看见南哥站在路上,等他从背夫手里拉过我,问了句“你还好吧?”,我当即崩溃地坐在那里哭得一塌糊涂。
我又一次高反了。坐至门槛上,目光呆滞,抽噎未止,机械地往嘴里灌着他们烧好的生姜红糖水。
![]()
以后多次回想这一刻时,我觉得自己当时像个失忆者,空洞、呆滞地注视着屋外,后来,一个情景触动了我——不远处,有不少人正向营地前方的一个山坡走去。竟然,还有人在往前走?
趁大家忙着收拾,我把一个热热的水瓶揣进衣服里,独自往坡上去了。
就在我盯着已经走在上坡路上的南哥的身影慢慢往上时,聚在餐厅楼上的领队和队友从窗户里看到了我,随后来到餐厅的队友也看到了我,于是我瑟缩着身体,摇摇晃晃一步步向坡上挪的样子全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观景台大约一百多米的高度,我上到了被十余座玛尼堆围绕的山顶。站在山崖边,四周群山环绕,但风大得几乎要将人刮倒,我放了一块石片在玛尼堆上。
![]()
一个小时后,当我回到餐厅,荣幸地被大家赐予了“勺子”这个称号(新疆方言,傻子的意思)。我无法解释是什么促动着自己当时状况下的行为,也无法描述站在那个比营地位置更高一些的山坡上所看到的景致,更无法说清山坡的高度、雪峰的耸峙以及山顶的玛尼堆、经幡和不停向上的人群,所给予我的暗示。
我只记得,那时我已经被风又一次完全吹透了,好冷呵!我浑身颤抖地站在那里。在我的身后,是巨大的褐灰色山体,壁立的岩体上满是挤压和摧动所形成的褶皱,密密而布,蹉跎坎坷。而我的面前,环视过去的,是安娜普尔纳丰收女神麾下众列雪峰,极致的雪质、冰魄,充满着野性、荒凉的山麓,在强烈的阳光和清冽的空气中,以高远而苍茫天宇之气,紧紧地攥住人的心魂。
我想,我只是一个贪心的人。(是的,我真的真的是一个贪心的人。)
当我站起身,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就是想多一些,亲眼去看尽这世界。
![]()
五、我需要一匹马
早上 6 点,背夫们就来我们的屋前敲门道早安,顺便找些吃的东西。站在门口,勾唐比画着跟我说了半天,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今天要上陀龙垭口,他可以帮我背包,并带着我走。我点了点头。
于是,抓紧收拾好,准备前往餐厅会合出发。屋里已经冷得出现冰碴了。等我跟着勾唐摸黑出门,抬脚就是上坡路,没走几步,竟然就迅速回到昨天从陀龙费迪到高地营地崩溃前行时的那种状态。这还只是在营地,我的信心彻底溃散。
我决定骑马过垭口。零红蝶看看我,又看看坐在旁边的南哥,点头许可。我知道,即便我不骑马,领队也会在垭口等着我最终到达那里,因为我是他的队员。还有南哥,无论 2000 米海拔的路,还是 5000 米以上海拔的路,南哥都会一直带着我走的。可是,我无法判断自己到底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到垭口,尤其还有下山的漫长路程,也许可以再仔细衡量路程和难度,可我还是这样决定了。
订好了马,店老板指着墙上的挂钟跟我说了一大串话,我大致听明白了——他说徒步过垭口需要四个小时,骑马要用两个半小时,所以马夫带我可以晚于大部队出发。
7 点了,大家都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我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背夫们都过来安慰我,勾唐还是那样笑吟吟地比画着说:“Slowly,slowly !”拉仁还是那种说起话来眉飞色舞的表情,南米德普看着我没说话,只郑重地点了点头。
大家陆续离开餐厅出发了,我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们全部出门,才坐回墙角的长凳上。
![]()
六、海拔 5416 米,陀龙垭口
9 点 10 分,天已大亮,马夫扶我上马后,他骑上马,牵着我的马缰绳,出发了。
也许是骑在马上的关系,山路在我的眼里不那么险恶了,周围的山势也并不像我昨天到达所见的那般陡峭。雪薄而稀拉地覆在阴面的山坡上,而朝阳面不时出现光秃的山岭,山体随着大片的滑坡铺满了细碎的石块。只是在前方,出现低缓、平圆的雪山。
我的马和马夫起初还能相跟而行,但后来路变得更为狭窄,马夫便将我的马缰绳交到了我手上,让我自己骑着马走在前面。这匹马儿很是温顺服从,我希望它能快点时,嘴里发出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含义的呼哨声,脚跟轻软地磕一下马肚子,它就很明白地提起了速度。而我也可以随着它的颠覆摇摆调整我身体的幅度,与它呼应而行。
山路愈发崎岖,不断出现之字形的陡坡,寒意早已渗透了全身,脚趾生疼,握缰绳的手也冻得僵硬,但阳光已经照亮了整个山谷。一片平地就在这时出现了,石屋、佛塔、经幡群还有正在兴奋地拍照的徒步客和背夫们,原来,这就是陀龙垭口了。
我们就这样抵达了 5416 米之地。此时是北京时间 10 点 10 分,距我骑马出发刚刚 1 个小时。
![]()
在石屋前,见到了一直等着我们的零红蝶,原来第一批队员不到 9 点就到了垭口。后到的队员先后挤进了小茶屋,这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屋了。我们都要了热咖啡,围着个小火炉烤火。茶屋空间太小,不停地有刚到达的徒步客挤进来取暖,我们刚暖和过来就赶紧让位给别人了。
山口风很大,庆幸的是天气晴朗,艳阳昭昭,我们和一大队外国徒步队员围在 5416 的标志佛塔和经幡群前轮流拍照。当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用手拨起挡在石碑上的经幡,露出上面写着的“欢迎到达 5416米……”的字样,又和背夫一起举着另一块也写着“Thorung La Pass (5416m)”的牌子拍着纪念照时,有些犯蒙,这真的是我们从海拔700 多米出发,徒步行来,上升到的那个垂直高度吗?
陀龙垭口 5416 米的海拔,才刚刚是喜马拉雅南麓平均雪线的高度,这与我在自己家门前经常能眺望到的海拔 5445 米的博格达峰,无法归为一个层面来理解。附近是六七座海拔 6000 米以上的山峰,四周积雪斑斑,大片裸露着碎石地面和山体的陀龙垭口,并非是以奇异的风光和壮美的山色,而仅仅以大环线上的一个海拔象征存在着。
![]()
七、疯狂地下降
马夫将我送到陀龙垭口,就返程了,此后的路,我便又能与队友并肩而行了。
一离开垭口,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传说中“大环线上最疯狂的一段下坡路”——海拔骤降 1600 多米的 10 公里路程,看着脚下之字形往复密布的山路,和远处山谷中尚且遥远的那一片村庄,不得不提起精神来。
山路上布满了带着棱角的碎石,背夫们像突然被放出笼的小兽,沿着羊肠小路轻巧地侧身向下快速蹿行,我们则按照领队的交代,沿着人工开辟的规则山路开始了无数次的转弯下行。
![]()
即便一直用登山杖撑着,不时也还会踩到碎石影响身体平衡,或者在光滑陡斜的坡道打滑,还有对膝盖过度劳损的顾忌,都使下山的过程变得谨慎,也渐渐让步履蹒跚的徒步者依次排成了队列。山路并不轻松,但毕竟海拔是在下降过程中,心里也慢慢地放松下来,开始有更多的氧气缓缓充进肺里。
身后传来驮队的铃铛声,是一群驮运物资的骡马,我们紧急避让,驮队在路上荡起尘土,晃晃悠悠地快速通过了。铃声当当不断传进耳际,令我想起一直喜欢的一首歌《Karma》,它是电影《喜马拉雅》主题曲,一种草木与天地之间的语言,我曾经听着它在大香格里拉路上拜访神山,行止水云之间。
那空灵秘语般的吟唱,始终镌刻在我的耳际空间。此刻,我就在喜马拉雅山麓,那清晰节奏中的藏音梵语,像就在山谷中回响,我的气息渐渐与它合拍。
![]()
八、又一年
时隔一年之后,我又一次随队进入安娜普尔大环线徒步。
2014年10 月 31 日,一早我们的徒步队伍准备从马南出发了,我依然早早站在楼下,等候集合。看着牦牛客栈商品橱窗里的红牛,我想起去年零红蝶说过的话,“走不动,喝红牛也照样走不动”。去年我的确是从马南买了红牛,一心想要努力,却走得很崩溃。
一年了,能再次走在这条大环线上,我掂量着自己,还是稍感忐忑。
走出马南镇,离开竖立佛龛标志的村口,前方是环绕山坡不断上升的道路,又一座佛龛耸立在山路转弯处。路口还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在这已经见不到森林的高海拔地带,这棵树十分醒目,更高的山坡上则是正在晨风中飘动的经幡。
![]()
走到这个高坡上,也适应了从起步时就开始的海拔攀升。回望身后开阔的河谷,在清早的阳光照耀下,流淌的马斯扬第河在宽阔的谷底分流成数道优美的曲线,回转蜿蜒,这曾经在低海拔处汹涌奔腾的河水,在此却身姿曼妙,如晨浴中的少女。
流云如白色的飘带从山峰顶抛向天空,以伸展的姿态凝滞着,在曙光的映照下,更如纱般纯洁。远远地眺望中,马南错落的石板屋燃起的炊烟,房屋上方竖立的经幡,都在逆光中散发出飘然仙韵。
地势起伏中,山路向前延伸,河谷渐渐收窄,覆盖着积雪的山峰连绵成一体,只在蓝色天际上呈现出起伏的山脊曲线。山体中部是裸露着的山崖和岩层、植被,它们带着沉积千万年而形成的复杂色泽,每一道褶皱里都有着深厚的意味。再向下方,褶皱如裙摆般散开,滑坡将积雪与泥土糅合渗透,像牛奶与咖啡的调和品,又像岩浆与火焰的凝固体。
岩羊们又出现在山坡上,垂颈觅食,鹰隼鼓风游荡,河水在山谷之下流淌,我们默默行走,感受着山野的静谧和纯粹的孤单。
![]()
九、陀龙高地营地
11月1日, 我们从雷得尔(Ledar,4200米)出发, 这一天海拔将攀升到 4900 米。我们用了 4 个小时,才到达5 公里之外的陀龙费迪。趁着午间天气晴好,继续前往陀龙高地营地。
这段犁沟般的峡谷,是在冰川运动中由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这些山体从最薄弱处切开,推铲冲刷成的。我们的路便在这峡谷下方的冰川碛石堆之间。在我去年到达此地时,碛石凌乱,四野荒芜,今年的暴雪令山野被积雪覆盖,碎小的碛石埋在雪里,深雪之中是人们踩踏出来的曲折狭窄的步道,时而雪埋腿脚,时而坑洼滑动,但路始终是畅通的。
到达高营地之前是最后一段陡坡路——夹峙在高崖之间如门洞一般局促、怪石嶙峋的通道,我慢慢地向前挪动,队友们中间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已经攀上高坡地带的人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之中了,前方的路好像通向天际,又好像就在那里被阻断了。转身回望,身后的人还像在一道陡梯的后端攀爬,尽管感觉自己没有力气了,但也明白,一步步坚持下去,不久就能到达了。因为我来过,心中敞亮。
![]()
陀龙高地营地,我再次到达时,一路走得都很清醒,只在最后一段陡坡上到营地客栈的路上,有点恍惚,似乎听到站在路边的南哥问:“你还好吧?”记得去年走到此处时,在南哥的问询下,被拉仁搀扶着的我大哭起来。可此时,当我抬起来,营地上原来我们住过的石头房子依然灰沉地陈列在山坡上,队友们已经进入客栈院中。
陀龙高地营地客栈的老板还是那个戴着厚厚酒瓶底眼镜的男人,他依然坐在柜台里收账。我很想表达自己再次到达的兴奋,过去比画着跟他轻声说,我去年来过这里,腿伤了,租过马……他看着我,随即问了我一句,意思是,你还要租马吗?我赶紧退后一步,摆着手大声说了句:“NO !”
![]()
等我积攒好了力气,感觉气息也顺畅了许多,出门准备上观景台,天气已经有了明显的转变。到了下午山里变天的时间了,四周浓云聚积,沉郁汹涌,深海波涛般压叠而来,似乎想要狠狠地将这大地上的一切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慢慢向坡上走去,积雪很厚,路又陡又滑,但有一条人们踩出来的雪道,借助着下山的邻居哥给我的一支手杖,我终于又一次上到了山顶。
站在山顶眺望前方,天色虽然阴暗,还时有阳光从浓云中穿射而来,眼前的一切都是具有生命力和温度的,是我久久惦念又重新回来的地方。这万仞高山,这大地上的雕塑,我再次面对着它们,就已经深深地满足了。
环绕着山顶的玛尼堆群转过之后,我又在附近拣了一块石片,放在了其中的一堆上面。我肯定是无法辨认出,去年我曾在哪一堆上面放下了哪一块石头,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步伐,我的呼吸和我的动作,那些与此刻,似乎只相隔了一秒。
![]()
十、陀龙垭口,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1 月 2 日,早晨 6 点(当地时间还不到 4 点),我们已经聚集在高营地客栈的餐厅,受到前些日子雪灾山难的影响,准备前往陀龙垭口的徒步客不多,一早出发的也仅仅我们这一队。
出发前,零红蝶郑重向大家交代,希望全队能保持一致的步调。我明白,这是对我这样步伐慢的人的照顾,也是督促——在大家都慢下来等着你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停下了,必须要跟上大队。
天还漆黑一片,我们依次列队站在山坡的小路上,背夫也一起站在我们的队伍中。海拔 5416 米的陀龙山口(Thorung La Pass)就在 5 公里之外,这又是一次告别和出发。面对坡下客栈的灯光,不免让我们都生出些悲壮的感觉。
经过暴风雪的洗礼之后,这段通往垭口的山路,不再只是通往一个海拔高程点,还通往曾经有许多人陷入绝望无助和失去生命的地方。
![]()
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与一年前相比,此时我的头脑并不混沌,我的双腿也没有灌铅般的拖坠感,整个身体都处在一个很正常的状态,也许这“正常”不过就是,我并没有被我意识中的高海拔困境所击垮。
邻居哥站在我的旁边,后面是孙老师、飘絮、快门线、跑焦和几个背夫。零红蝶在最前面,青衣、一米、阿布、牛牛跟着他。我随着大家一起沿高坡努力行进。山路陡直上升,偶尔抬头的时候能看到一面倾斜的天空,它一直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璀璨的星子在天幕上闪闪烁烁,缓缓流泻。可我顾不上欣赏这么美的夜空。我只能低着头一步步向前,紧紧盯着脚下由头灯照亮着一片地方,似乎天地小到只是这样容纳双脚迈过的一隅。
前方的队友逐渐拉开了距离,远远看到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山坡上攀援着,队伍已经从我这里分为两截,我竭力向前迈步,但依然不能快速跟上前队,反而走得越来越吃力。这个速度对我来说的确已经超过了极限,如果不是在队伍里,我可能早就停下来休息了,可现在相当于是一边走路一边喘息一边调整着脚步一边平衡着气息,我渐渐有些不支。
不久,寒冷、缺氧和疲惫令我开始气息急促,浑身颤抖,身体也有些佝偻,这时邻居哥从身后推着我,说:“别停,走!”我不知道他带给我的这股力量到底有多大,可是我的确就一直在按他说得那样,不停!
不停!走!走!攀上一段高坡后,邻居哥又说:“这里可以缓一下。”我便赶紧站住平息两口气。他再说:“走!”我便又立刻迈步向前……
![]()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用去了多长时间,我想在我的身体里已经没有了对海拔 5416 米的恐惧,它被彻底赶走了——在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努力跟上前方队友,在我想着尽量不要拖慢身后队友的步伐,在我想要每一步都不要迟疑和停顿,在我终于和周围的世界成为一个节奏的时候,我完全沉浸于其中。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断迈向前方的脚步,一步不停,只想着一步都不要停……
就这样走着,渐渐我便也忘了,这段路通向那个蕴集诸多含义的陀龙垭口,忘记了,这里是海拔超过 5000 米的山地。我只是看着前面的队友,知道自己只要努力就能跟上他们,走完这一程。只要努力。
![]()
十一、谁能说出,道路伸向何方
零红蝶在前面的山坡上喊了一声:“看啊,天要亮了!”他喊出这句话的声调,竟像一个游吟诗人面对碧海长天的慨叹,似由此开始吟诵一首长诗……
虽然在路上已经感觉渐渐转亮的天色,可一直只顾着低头看路。这一下,我们都停住脚步,回转身去。此时,云霞涌动,从地平线下升起的阳光,正在穿透着昼夜交替时的屏障。我们周遭的山地都被积雪覆盖,雪地上只有深深的一道印痕——徒步者们蹚出的这条路,在我们的脚下,无止无尽地延伸。
谁能说出,道路伸向何方,岁月流逝何处……
天亮了,我站稳脚步,转过身去,那是我在低头俯身艰难行走时,已经隐隐感觉到的光亮,于是我便面对着那光亮——那一瞬间,眼泪涌出,喉咙间轻轻发出了声音,我的心在胸腔里如冰河融化般缓缓舞动,面前的所有,全都沉浸在金色的日出之光中。在模糊的视线中,我看到了自己,伫立于陀龙垭口的自己,被这神光映照,连呼吸也变得灿烂透明……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在东方的天际上,天色清亮明朗。一些薄薄的云絮游移在山顶,阳光自云端投射而下,耀眼的光辉从天际落向积雪的山野和我们走来的山路。
![]()
![]()
我终于有机会取出相机,手指颤抖地按下快门,山野上空的朝阳迸射出无数光柱,就在那一瞬间,我们和陀龙山谷一起,汇入了时光的流向。
垭口的标志,经幡群,小茶屋,都在不远的 5416 米处了。我们即将走到这一程的最高点。可是,在看到日出之光耀亮世界的那一刻,仿佛一切都完成了,如再一次的洗礼。
星光已经全都隐去了,天空泛起淡淡的青白。在半空飘浮的云仿佛凝固着,万丈光芒从山脊后喷射而出,耀眼闪亮,自天际漫漶而来的光明,瞬间就照亮了大地、雪山和我们脚下的冰雪之路。云霞显出灿烂的金黄色,这色彩晕染着天空,为它添上了无限生动的韵律。
此刻,大地金光灿烂。
——节选自《南麓山野》 骆娟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6年11月出版
![]()
你们慈爱大地上的一切,上苍就慈爱你们 ‖ 南麓山野
(图片来自于徒步队友 孙月亮 零红蝶 飘絮如风 南山牧民 跑焦 高原红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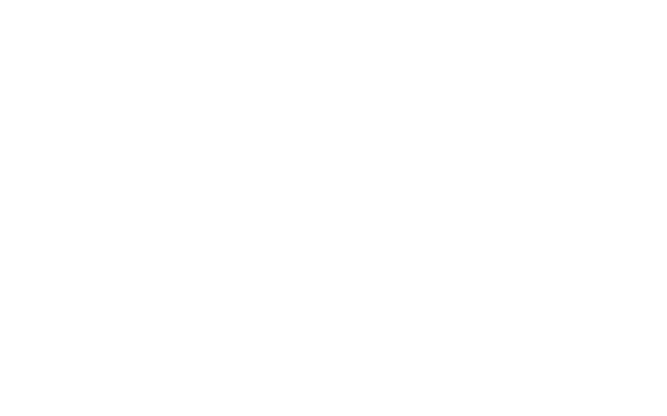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