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学去
懵懵懂懂之中,幼年便飞逝而去,我也该到上学的年龄了。而对于上学,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概念,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学校人多,很可能更热闹、更好玩儿。于是,几天纠缠着让母亲快点缝制新书包,让父亲买铅笔、像皮、作业本儿,打算从此告别野孩子般的生活,快快乐乐上学去。
大约是1973年,一个秋天的早晨,天刚刚放亮,我便背着我的新书包,急匆匆去找我的表哥利平,打算早早去学校。表哥和我同岁,只是生日比我靠前,平日里我、弟弟和表哥总在一起玩儿,这一回,我们最终甩下了小屁孩儿弟弟,和表哥高利成了同班同学。
学校在村子的西头,学校北面的坡顶上原有一座庙宇,也不知是财神庙还是姥爷庙亦或是喇嘛庙,但庙宇早已不在了,只剩了一些残砖断瓦散布在那里,上学之前,我们曾经常在那里玩儿,有时候还扒在学校的墙头上,羡慕地望着学生们在校园里读书、上体育课、做早操,如今,该是我们也加入他们行列之中的时候了。
我和表哥被分到一、三班。这个班是复式班,也就是一年级和三年级混编在一起,如果第一节上一年级的算术,那么第二节就上三年级的语文,第三节上一年级的语文,第四节上三年级的算术。总之,学校不算大,分为一、三班和二、四班,五年级由于加入了其它村子的学生,人数较多,于是单独设立一个班。
很显然,由于一批拖着鼻涕、穿着开档裤的小孩子加入,三年级学生突然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来,不管是课堂纪律还是作息时间,亦或是上早操、课间活动,一旦一年级新生有哪怕犯一丁点差错,总会被三年级学生讥笑嘲讽甚至批评喝斥,而我们只能乖乖听话,否则就会被他们打小报告,挨老师的批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年搞复式班,除了教室和师资不够的原因外,便于管理很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哩。
原以为,进了学校,会更加好玩儿、热闹,可一旦开始上课,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像般美好。由于学前没有上过幼儿园,家里人也没有教过什么字,所以老师讲的课基本听不懂,什么笔划、拼音、阿拉伯数字、加减法,好像听天书。我和表哥高利同桌,一边听老师在讲台上认真讲课,一边莫明其妙地左看看、右看看,见别的同学也都是一脸的茫然,于是我俩相视一笑,便在课桌下面开始玩儿解头绳之类的游戏。课后,老师布置了作业,我们也领受了“任务”。
放学后,我和表哥相跟着,先是给家里拔猪草,接着又与弟弟他们一伙人玩儿了一回打仗的游戏,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突然间想起了老师留的作业,于是取出书本,在煤油灯下开始做作业。直到此时,我才发现,老师留的作业我居然一个题也不会做,比如“人”“头”“口”字怎么写,比如从“1”到“10”如何写。抓耳挠腮之后,我决定去找表哥高利,看看他怎么做。踩着黑漆漆的小路,我来到村东头表哥家里。一进门,发现他也正坐在油灯下,为作业的事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看到我来了,他好像遇到了救星,连忙向我求教如何做这该死的作业。不料,我也一窍不通,于是只剩了大眼儿瞪小眼儿。
眼看着做不出来,我们一时泄了气,都不知明天该如何向老师交差。还是表哥脑子活,他自信地说:“看我的吧。”我不知道表哥利平有什么妙招,不过他平时就很机敏,在日常疯玩的过程中,好多鬼主意都出自于他。等他做完了,拿过作业本一看,才发现表哥在每一个方格之中,都用铅笔涂了一个黑点,就当作一个汉字或一个阿拉伯数字。我一看乐了,笑着说:“好呀,这作业其实很好做。”于是,照着样子在自己的本子上涂了好多的黑点,算是把当天的作业做完了。自然,第二天,我们别出心裁的作业被老师拿着在全班同学面前“亮相”,并且挨了好一通的批评。从此之后,我们再也不敢做这样的作业,只好认真地开始学语文、学算术,加强训练,不会的时候也会向哥哥以及同学们请教。
校园生活虽然没有先前想像的好玩儿,可毕竟这里人多,再加上还有别的村子的学生,还是比较热闹,我和表哥利平在这里接受了人生的启蒙教育。
在初小所有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一位是李姓的语文老师,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大概在他的身上我识了不少的汉字;另一位是张姓的数学老师,还是校长,他脾气不太好,记得经常打骂学生,张老师和我父亲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胆子小,还算比较照顾,所以我并没有挨多少巴掌,可表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至少让张老师打骂过好几次。记得有一回课间,我和表哥翻过院墙,到学校北面的一棵大树下玩儿,见树上有一鸟窝,表哥利平自告奋勇在脱掉鞋就爬上了树,去掏鸟窝,只是时间不对,窝里既没有鸟蛋也没有小鸟,只好幸幸地下来。可下到半道,利平的裤子就被树枝挂住了,怎么折腾也下不来。眼看快要上课了,我也顾不上许多,只好丢下表哥,一溜烟跑回了教室——那节课正好是张老师的。张老师一进教舍,就发现表哥不在,便问大家谁见到了。我使劲埋下头,不敢看老师,更不敢言语。正在此时,表哥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教室。不用说,表哥挨了张老师好一通的骂。
时光一点点过去,我们也从一年级升到了二年级。这个时期,我和表哥的学业基本上处于混沌状态,不能说班里面最差,但至少处于倒数的位置,后来想想,怪时代?怪自己?还是怪老师?似乎都不能排除,但又似乎都不对。反正,这个时期,我们还是表现出半是学生半是野小子的行为,这让老师、家长很是头痛。好在,那时的学生很好当,课程少、作业少、学习比较轻松,没有任何人为分数、为排名而苦恼,更没有任何人为考试、为升学而劳神耗骨。
直到有一天,同班三年级的王五同学悄悄告诉我:“开始批林批孔了,千万别告诉别人呀。”至于什么是批林批孔,他没有说,我也不知道。管他呢,别批到我和表哥身上就行啊,如果挨了批,不但家里大人面前不好交待,而且还影响我们整天玩耍呢!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是根本不够资格的。没错,我们的小心思其实是一个国内笑话。
莫明其妙
我上小学的时候,读书实在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上课不紧张,学习很省劲,基本不留什么作业,隔三差五还要参加劳动,所谓劳动也就是帮着生产队拔拔荞麦什么的,并不累,而且还能吃上生产队给做的炸油糕、烩豆腐粉条,是一件既轻松又实惠的事情。
但那时也有些让人不太明白的事情,主要是大批判会。我们中心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星期要召集全中心的学生,召开一次大批判会,主要是批林批孔,“林”就是林彪,“孔”就是孔老二,林彪干的坏事就是要篡党夺权,可孔老二干的坏事却让我们十分茫然,比如“悠悠万事”“克己复礼”“唯此唯大”等等,听着好像是天书。
中心校正南窑村小学有一王姓同学,当时的作文写得非常好,他写的东西经常成为范文拿来让我们大家学习。于是,这个姓王的同学也就成了大批判会的最先发言人。
那天开会,姓王的同学意气风发登台发言:“林彪、孔老二是一丘之貉,他们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妄图克己复礼,我们革命红小兵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批判会结束后,有一个同学问姓王的同学:“林彪和孔老二是什么亲戚呀?”王姓同学一时语塞。又问:“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克己复礼是啥?”王姓同学又答不上来。再问:“孔老二早就死了,林彪也死了,我们红小兵还要革谁的命?”王姓同学仍然答不上来,反倒白了那同学一眼,气哼哼地说道:“莫明其妙!”
同村有一个姓张的同学这些日子有些不走运,接连挨老师的批评。先是他把自己的红领巾说成是“蓝领巾”,听到这个名词,有一个机灵的同学便向老师告了密。老师先是不相信,认为这个张姓的同学还算班里最老实的一个,怎么能把革命的红领巾说成是“蓝领巾”呢!于是叫来张姓的同学随便问了问,批评他不该这样污蔑这鲜血染成的革命红领巾,要求他端正态度,不能乱说乱动。
可是祸不单行,过了几天,张姓同学与其他同学玩儿的过程中,不小心将蓝墨水甩到了黑板旁边张贴的毛主席像上面,这下可惹了大祸。那个机灵的同学立即把这个十分严重的情况报告了老师。老师闻讯很快到教室里查看,果然,毛主席像上有一串蓝墨汁。胆小的老师不敢擅自作主,马上把情况报告了校长。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校长认为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即布置召开批判会,对张姓的同学先后两起行为进行口诛笔伐。
在批判会上,张姓同学首先发言,他说:“千错万错,我不该把红领巾说成是蓝领巾;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往毛主席像上洒墨水。我要向大家认错,要向毛主席认罪。”
这时,台下有一个同学举着拳头喊道:“我们红小兵是一颗红心,那你的心是什么心?”
张姓同学低声说道:“那就是蓝心呗。” 台下又有同学断喝道:“你往毛主席像上洒墨水,你居的什么心?”
张姓同学的头更低了,声音也更小了:“蓝心。”
从那以后,我们都叫张姓同学为“蓝心”。
有一次,我和表哥跟着村里的大人们,跨过浑河到镇上玩儿。刚到镇上,就看到一大群人围在一起,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和表哥利平也凑了过去。等挤进人群才发现,原来有一个老汉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四类分子”的纸牌,他身后还有两个背着麻袋的后生,三个人正在民兵的指挥下游街。只见这个老汉一边走一边敲着一面锣,先是“镗镗镗”敲三声,然后高声喊道:“四类分子杨成奎,支持儿子偷莜麦子。”如此周而复始,在二里多长的街道上来回游行。地、富、反、坏、右是当年明确要打击的对象,但“四类分子”是什么,我和表哥自然是不明白的,但支持儿子偷莜麦肯定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们跟在别人的后面,一边看热闹,一边听围观的人议论。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前几天镇上的西队麦杨上丢了莜麦,后来民兵侦破了案件,抓住了杨成奎和他的两个儿子,于是在武装民兵的押解下游行批斗,却不料被我们正巧碰上了。
回村之后,我和表哥学着样子,敲着一面烂洗脸盆,“镗镗镗”:“四类分子杨成奎,支持儿子偷莜麦。”一路喊下去,竟然吸引了村里好多人来围观。于是,我们玩儿得更欢了。为此,母亲还嗔怪地说:“这些灰小子,都喊了些啥?!”
直到后来大了点才明白,当年,大集体搞得红红火火,但家大人口多的杨成奎一家人常常挨饿,几个儿子整天在地里劳动,有时饿得头晕眼花,实在熬不过那个金色的秋天的时候,便大着胆子从麦场上偷了几麻袋掺着杂物的莜麦聊以充饥,却不料被发现了。听说,即使是挨批斗,杨家父子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游街批斗时会有集体提供的伙食,至少可以吃得饱。
如今,人们还记得那个近乎疯狂而愚昧的年代吗?
差点淹死
李校长真是我们学校的“红管家”,一向把我们中心校经营得红红火火,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张校长、郭校长,且在郭校长时期达到了顶峰。每年春秋两季,我们总会有十天半个月在田地里度过,做什么呢?勤工俭学!
中心校在西沟河西侧山崖下有一块校田,清澈的河水从东边流过。春天,郭老师每次带领一个班的学生来到这里,松土、打畦、修渠,然后种上土豆、大豆、萝卜、葫芦等;夏天,我们又来这里锄草、浇地、施肥;秋天除了收割校田之外,还要组织大家去生产队已经收割的庄稼地里捡拾麦穗、高粱、大豆、土豆等,所有这些收获的粮食作物,都按规定出售给粮站,然后补贴学校开支,据说单就勤工俭学这一项,我们中心校在全学区都是先进呢。
西沟河很悠长,从十几里外的地方曲曲弯弯,经过我们村的村西,一路奔向浑河。凡是流经的地方,榆树、杨树郁郁葱葱,十分茂密,形成一条绿色长廊。河的两侧,甩下一道道湾子,那里成了自流灌溉的良田。因此,每到春夏之交,人们就会在河道上拦起一道道土坝,然后修通渠道,引水浇灌,我们学校的校田也享受着这样的待遇。
有一年的夏天,我们三年级和五年级两个班的同学,在李校长的带领下来到校田,在炎炎烈日下,先是锄草松土,然后清理渠道,最后在上游土坝右侧沿着悬崖开了一个小口子,通过渠道,把清清的河水引入校田,滋养我们辛勤耕耘的校田。
天实在太热了,就像头上罩了一盆火,烤得人喘不过气来。李校长真懂得疼人,当任务完成得差不多时,他让一个老师带领女同学们先期回校,然后领着男同学们一齐来到土坝上,放心大胆在让大家耍水。同学们欢呼着,纷纷脱掉衣服,像一只只光滑的泥鳅,扑腾腾跳进齐腰深的水里。顿时,坝里面到处溅起了阵阵水花,荡起快乐的笑声。
我自小就爱水,从记事起,就和伙伴儿们在我家窑洞门前的溪流里玩儿泥、促鱼,遇有下雨溪水大的时候,还光着屁股爬在泥水里学狗狍,可直到上了三年级也没有学会,这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家里大人不让进深水玩儿,说在那里耍水是会被淹死的。从此,多数情况下,我会远离水塘。
不过,这一次有李校长坐阵,还有那么多五年级同学相伴,想想也没什么可怕的。于是,也学着同学们的样子,三下五除二扒光衣服,从岸边小心翼翼地下进水里,一步一步向塘坝中心移去。水先是淹过了小腿,后来是小肚子,再后来到了胸脯。此时,水里同学们正在互相泼水嬉闹,也有的捏着鼻子“钻沙”,好一会便从别处冒出头来,也有的“狗刨”着游向远处,更多的是捉对撕杀。河湾里打闹声一片。我看到,李校长正坐在岸边的土坎上,一边痴迷地抽烟,一边迷着眼睛望着河里的一群嬉闹的孩子。
然而,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被一浪接着一浪涌过来的水给冲倒了,此后怎么回事,竟然一点都不清楚了。也不知何时,我被同村五年级的拴杰拽着胳膊拖上了岸。拴杰问我:“喝水了没有?”我莫明其妙地说:“我不知道。”此时,他才告诉我,当时他正在我边上游玩儿,一转身却不见了我的踪影,只见我的一只手斜着伸出水面,这样才引导着他前来搭救于我。此时,李校长也走过来,见我没啥事,告诉大家要互相关照着点,别淹着了。但是,差点送掉小命的我却再也不敢下水游玩儿了。
是的,我这条小命是拴杰给挽救了的,虽然当时决心再也不去与水抗争,但天性使然,我还是没能抗拒水的诱惑。因为在我们村的南边、东边、西边、北边,均有河流或湿地,都有成片的塘坝舒展在那里,看着小伙伴儿们天天下水游戏,我自然也不甘寂寞,先是爬在水边拍打双腿,后来慢慢地深入水中并学会了“狗刨”,感受水的清凉,体会水的力量,接受水的抚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村的根文率先学会了“死人漂”,也就是仰泳。不用手把手教,也不用高手指点,没有几天功夫,我们居然都学会了这种最省力、最前卫的游泳方法。
从此,在摆脱老师了大人们视线的情况下,我们像打游击似的,去西沟河的塘坝、寸草滩的塘坝、八号沟的塘坝里游泳,并且很快在周边地区出了名,都说我们村的孩子们不怕水,再深也敢进去游玩儿。
在这样的锻炼之下,我的泳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但在本村游,还一直游到外村,游上了镇子,有几次还和同学们合伙,救过三个人呢,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反正,经过一次危险的举动,我不但没有被水淹死,反倒成就了一门小小技艺,虽然不精,但也足够丰富人生的经历,足够回味自己那清涩的童年。
![]()
吴欣,男,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人,内蒙古作家协会、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诗词学会会员,在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多篇,出版文学作品集《赤黄的爱》,与人合著《西口第一镇》《盛乐览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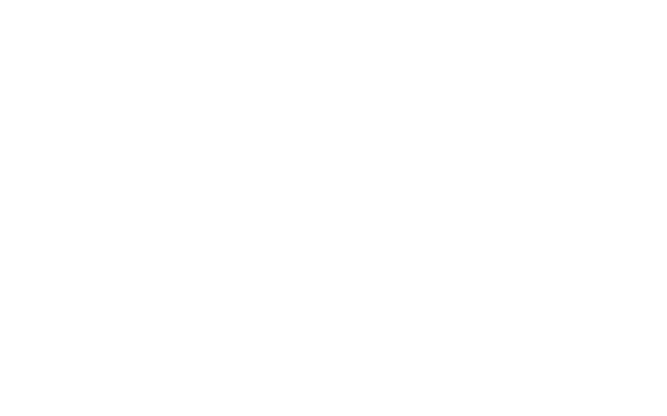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