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丽仁阁文化艺术馆[顺林艺苑]
草虫寄意,童趣绵长——周德尧《童趣》国画的多维艺术审美
在周德尧先生的国画《童趣》里,两只蟋蟀、一爿残罐、几根草叶,不仅是笔墨的铺陈,更是一场关于童真、童趣与童年的诗意回溯,在艺术研究、画理探索、自然观照、人文情怀与美学表达的交织中,构建出动人的审美场域。
一、童真之境:生命本真的艺术显影
童真的可贵,在于对世界毫无设防的好奇与纯粹。画中蟋蟀的刻画,尽得“真”之妙趣——它们并非程式化的符号,而是带着生命的跃动感:一只棕褐蟋蟀振翅欲鸣,另一只乌黑蟋蟀弓身似斗,触须纤细如丝,足肢纹理毕现,连虫身的甲壳光泽都被细腻捕捉。这种对昆虫体态、神态的精准摹写,源于画家对自然生命的童真式观察——以孩童般的眼睛凝视草间虫豸,将其视为有性情、有故事的“小伙伴”,而非 mere 生物标本。
残罐与草叶的搭配亦见童真意趣。破碎的陶罐带着岁月的斑驳,却在画面里成了蟋蟀的“游戏场”;一根草茎斜穿碎陶片,似是孩童无意间的摆设,又像一场微观世界的“装置艺术”。这种对日常物什的艺术化重构,复刻了童年里“以残罐为城堡,以草茎为长剑”的游戏想象,让观者瞬间跌回那个把平凡物什玩出万般花样的童真年代。
二、童趣之味:笔墨间的游戏精神
童趣的内核是游戏性,在《童趣》中,这种游戏性通过画理的突破与笔墨的灵动得以释放。
从画理看,传统草虫画多追求“小中见雅”,而周德尧先生却在“雅”中注入“玩”的意趣。他以工笔的精细勾勒蟋蟀的肌理,又以写意的笔墨晕染陶罐的古旧质感,工写结合间,打破了技法的边界,恰似孩童游戏时“不守规矩”的创造力——想让蟋蟀逼真就细细雕琢,想让陶罐随性就泼墨晕染,这种技法的自由切换,正是童趣“玩得尽兴”的艺术转译。
笔墨的灵动更强化了童趣感。蟋蟀的触须以中锋淡墨轻提,似有微风拂过的颤动;陶罐的釉色以赭石、墨青层层积染,却在边缘留出水渍般的晕痕,仿若孩童涂鸦时的偶然“败笔”,却意外成就了生动。这种“笔随心走,趣自笔生”的笔墨状态,把观画者带入“蹲在草间看虫斗,不觉日落半天”的童年游戏场景,让童趣在笔墨的流转中鲜活可感。
三、童年之思:人文与自然的双向共鸣
童年是个体与自然、人文最初的深度联结,《童趣》恰是这种联结的艺术定格。
从自然维度看,画中蟋蟀、陶罐、草茎皆取自田园野趣,是童年与自然最朴素的对话载体。周德尧先生以写实又写意的手法,让自然生命在宣纸上“复活”——蟋蟀的鸣叫似在耳畔,草茎的触感若在指尖,这种对自然细节的极致还原,唤醒了人们关于“捉蟋蟀、捡陶片、编草哨”的童年自然记忆,完成了一次个体与自然的跨时空共鸣。
从人文维度看,画面题字“寻遍崎崚听颂虫,只缘此物最情浓”,点出了中国人对草虫文化的人文情结。斗蟋蟀、赏虫鸣本就是民间童年文化的一部分,画家以笔墨定格这一文化场景,让个体童年记忆升华为群体人文乡愁——那些关于虫鸣、关于乡野游戏的片段,是中国人文脉络里“亲近自然,寄情小物”的精神缩影,在《童趣》中被温柔唤醒。
四、美学之境:微观世界的宏大审美
在美学层面,《童趣》实现了微观题材与宏大审美的辩证统一。
从形式美看,画面构图看似随性,实则暗藏章法:两只蟋蟀一上一下、一棕一黑形成视觉呼应,残罐与碎陶片一主一次构成空间层次,草茎斜穿打破呆板,题字与印章点缀边角,让微观的草虫世界具备了“可游可赏”的山水格局。这种“以小构大”的构图智慧,把童趣题材提升至经典的美学范式。
从意境美看,画中无孩童形象,却处处是童年意境。蟋蟀的灵动、陶罐的古拙、草茎的野逸,共同营造出“草间天地,虫趣无穷”的诗意氛围,让观者在微观物象里见出宏观的童年哲思——原来最动人的童趣,藏在对一只蟋蟀的专注凝视里,藏在对一片碎陶的游戏想象里,这种“于细微处见真趣”的意境,正是中国美学“咫尺千里,小中见大”的生动诠释。
周德尧先生的《童趣》,以草虫为媒,以笔墨为桥,在童真、童趣、童年的情感维度里,交织起画理、自然、人文、美学的专业思考。它不仅是一幅草虫画,更是一封写给童年的艺术情书——在这封情书里,我们看见自己蹲在草间的影子,听见了记忆里的虫鸣,更读懂了艺术对生命本真、对人文乡愁的永恒眷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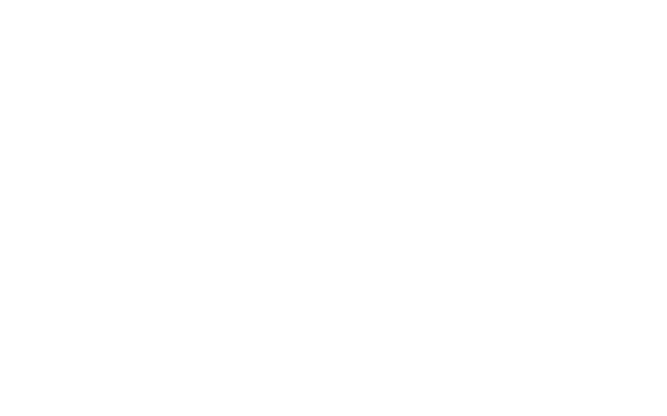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