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到于她而言
羊角花纹的马鞍就是奢侈品
她的爱却一点都不普通
她的爱是我的奢侈品
小时候,我在母亲的背上
草原的风一如平常
灰骏马没有换来拖拉机
鸡蛋被悄咪咪换成了冰棍
冬天的冰柱子也进了肚子
都远不及炒土豆焖馕
那么普通又绝无仅有
长大后,路途无穷无尽
我笔下的文字一如平常
推成小山的报纸和杂志还没有看完
精心构图的摄影作品没来得及装裱
她是我最普通最忠诚的读者
无忧无虑的日子却每一天都是新的
老去,日子越过越慢
身体的老毛病一如平常
医生多加了几瓶点滴
水漫过渠淹了院子
松开了握紧的手
是您最普通的安详的表情
轻轻地把您放进大地的摇篮
造物主一定没听到我的祈祷
现在,又回到老房子
细数的日子一如平常
菜地和水渠没有和解
我们没来得及和您好好告别
母亲用她普通的一生
哺育了我、抚养了我、教导了我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延续着这普通又独一无二的爱
母亲离开已经三个多月了,她遵守了她最后的诺言,没有麻烦我们任何一个孩子。除了确定母亲已经离去的那个瞬间,我还是会时不时想起母亲。
“爸爸,您看!是奶奶的马鞍!”叶尔达纳把母亲的马鞍一把抱到怀里,呜咽起来。我知道,可怜的孩子是想奶奶了。
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母亲,妻子和儿子去乡下的房子。我们修理院子,松松土,种种菜,贪婪地呼吸新鲜的空气,不亦乐乎。但,今年的夏天,截然不同。这是继母亲去世后我们第一次来乡下的房子。
![]()
![]()
![]()
不止是叶尔达纳,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念母亲。我和妻子把达那抱在怀里,想去安慰他的我们,眼泪却止不住的流。至亲离去的那一瞬间通常不会使人感到悲伤,而真正会让你感到悲痛的是打开冰箱的那半盒驼奶,是那安静折叠在床上的棉被,是那长在院落石头缝里的杂草,而在此刻,是叶尔达纳怀里落着泪滴的母亲的马鞍。
“好了孩子,不要再哭了,你奶奶是长命的人,哭得太厉害是不吉利的。奶奶要是知道你这么哭,她会难过的。你奶奶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啊。只希望她的后代也能像她一样活到90岁高寿。”我也只能勉强用‘不吉利’来止住我们的眼泪。‘这样做不吉利。’是叶尔达纳的奶奶跟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不能做不吉利的事”,是母亲从小给我们种下的“祈福种子”。
叶尔达那一边用袖子揩去脸上的泪痕,一边叫我:“爸爸,爸爸!您把奶奶的马鞍找回来时,奶奶为什么会抱着马鞍哭?”“哦,孩子,这个马鞍是你奶奶年轻时,她父亲特意为她定制的。她大概是想起了什么吧。”我简短地回答了儿子的问题便“逃离”了。
![]()
![]()
![]()
母亲18岁和父亲喜结良缘,这个银饰马鞍是我外公在母亲出嫁时找来全村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嫁妆。马鞍被母亲之前的邻居借走之后的这些年,她经常谈起父亲给她的马鞍。我四处打听当时邻居爷爷的现住处,终于把母亲的马鞍带回了家。
母亲看到马鞍,眼里难得闪过如同见到外公一般的欣喜,还记得她眼里泛着泪花,用松枝般的手轻轻描摹马鞍上镀银的羊角花纹。从那以后,马鞍就被母亲存放在乡下的房子,留作对外公的念想。物是人非,母亲用马鞍怀念外公,我们用马鞍悼念母亲。
母亲离开已经三个多月了,以前经常听到母亲念叨:“我活到这个岁数已经满足了,希望不要再给我的孩子们制造麻烦,在他们之前离开这个世界。”母亲果然没有食言,即使在离开前,也从未找我们照顾她的起居,我的母亲啊。
“妈妈,妈妈,您怎么了,请您睁开眼好吗!”病床前我攥着母亲的手,把头埋进母亲的怀里,感受到母亲的呼吸变得极其微弱,吊瓶的点滴也似乎陪着母亲变得很慢很慢。
“医生!护士!快来看看,我妈妈怎么了?”我没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把他们叫来的,床边就围满了人。母亲像是要把手抬起来似的张开五指,又紧紧地合起来了,用另一只手用力地握着我的手,也许是想告诉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人要像这五根手指一样团结互助。
我泪流满面哀求着医生救救母亲,他们像不忍开口告诉我母亲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事实,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摇头,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哀嚎道:“母亲,我们不是约定好这次出院后一起去拜访哈巴的舅母家吗?您怎么就这么走了?您怎么可以失约呢?”
这些年母亲经常到医院小住,检查她的老毛病,但治疗结束就回家了,我们也从未把母亲住院看做是严重的事,更没想过有一天她真的会离开我们,永远的,完全的。甚至直到这一次我们也觉得和往常一样,母亲会回家的。母亲离开的那天上午,姐姐来医院看望母亲,她像有预感似的担心不已,我还在宽慰她:“你别担心,妈妈明天就好了,今晚我留在医院照顾就行,你先回去忙吧。”
![]()
![]()
![]()
![]()
人们总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迷途。悲痛欲绝时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的。只记得老人说过人离世的时候要把下巴包扎起来,我把母亲的身体摆正,用母亲头上的白头巾围下巴,轻手轻脚地护着,小心翼翼,怕弄疼她。哥哥们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布满红血丝的眼球凹在眼眶里。大家都清楚,也不是不能哀号颓迷,何等的毁顿都不足为奇。可是这人世间最后一件和她有关的事,我们都尽力克制着体面。
接下来最让我们为难的事情是怎么告诉我的儿子叶尔达纳。天还没亮,我们都心照不宣不忍心叫醒熟睡的叶尔达纳。突然,他像感应到一样,反常地冲出自己的卧室。他睡眼惺忪,疑惑地叫了声“爸爸?”他的声音抖了起来,“家里怎么这么多人,怎么了?”我的眼泪再一次败下阵来,只能试探着开口:“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爸爸告诉你一件事,可是你不准哭哦。”他向我保证:“好!”“你知道奶奶年纪大了,她太累了,所以她要好好睡一个长长的觉了。”“啊!”他喊到:“奶奶在哪里?奶奶去哪了?”我可怜的孩子哭成了泪人。“奶奶为什么不能再多活几年,为什么要丢下我们,以后谁陪我玩呢?我要我的奶奶回来!”我把脸贴在他的额头上哽咽:“没有办法,我们都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
![]()
![]()
![]()
我一直忘不掉父亲离世前一天,乡下院子的围墙因为被水淹而倒塌了。而就在母亲离世的前一天,浇菜的水漫过渠把乡下的院子淹了,像是某种预兆。我的心被揪起来,又被沉重的焦虑紧紧裹住。我不敢往坏处想,但又不自觉地一遍遍在心里祈祷:请造物主保佑我的母亲。我不争气地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我自己也骗不了我自己了。
过去母亲常跟我说,人终有一死,没有谁是可以活万年的,但是后代可以传万年,等去世了让我把她安葬在父亲旁边。每次她谈到这件事我都会打断她,让她别乱说,是出于本能地担心和恐惧。有一次叶尔达纳听到了奶奶的话,抢先说到:“奶奶您一定会活到一百岁的,以后会看到我结婚的。”母亲听了哈哈大笑:“我的宝贝孙子,希望如你所愿看到你们的婚礼。”接着亲了亲叶尔达纳的脸。现在,我们做个懂事的孩子,把母亲安葬在父亲旁边。
4月23日早晨,送母亲上远路的灵车碾过母亲曾经走的路,却走向了和家相反的方向。车走得越快,我的心痛得越厉害,这意味着我即将把母亲交给这冰冷的大地,离别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天空阴沉沉的,整个村庄也悄无声息。母亲好像是在不舍地跟她的故乡和乡亲们道别。那些曾经和母亲一起种下的树好像也低着头,向母亲道别。生命来去也许自有定数,路径不一,步调错落。
看着留在身后的老房子,我坠入回忆的长河:母亲您是否还记得,我们懵懂的孩提时代在这里度过,意气风发的少年时期也是在这里度过。您还记得那次吗?您背着我去阿依特哈泽叔叔家,我看到邻居叔叔家的拖拉机吵着您帮我把它要来带回家。邻居叔叔听到我的话,跟我约定拿他的拖拉机跟我的灰骏马交换。天真的我真以为只要把我的马儿给邻居叔叔,他就会把拖拉机送给我。灰骏马可是我们家得力的小助手呀,我回家后还吵着闹着让您和父亲带着马儿去换拖拉机呢。冬天的时候,我和姐姐会一直等着您洗衣服的日子,等到您要洗衣服的时候我和姐姐会把雪堆起来,再把洗过衣服的水洒到雪堆上做成滑冰梯,玩得不亦乐乎。母亲,这些您肯定都记得的,对吧?
小时候我总跟您说,等我以后长大成人后到城里工作、结婚立家,到时候我会把您也接到城里。您总是笑着回我:“等我的孩子成为男子汉会报答我们做父母的,但愿我们能活到那个时候呀。”
母亲啊,你知道吗?每次那位喊着“卖菜!卖菜!”的汉族阿姨过来时,我和姐姐为了吃冰棍,会偷偷去拿家里的母鸡刚下的蛋跟阿姨的冰棍做交换,等到晚上我们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可您却说:“今天的鸡蛋比较少,可能是鸡吃得不够饱。”我们还窃喜以为您没有看穿我们的小把戏,可是母亲啊,您早就知道了吧。还有冬天的时候,我们谎称要去拾牛粪,其实是跑去掰屋檐结的冰柱子吃,所以我们才总是咳嗽。对不起母亲,一直没有告诉您和父亲,让你们操心了。还记得我和叶尔兰哥哥一起去峡谷捡烧火用的木柴回来时,您会做好炒土豆焖馕等着我们,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美味的饭。我是您最小的儿子,您把我当宝贝看待,我吃母乳长大,甚至读了一年级我还闹着要吃母乳。我的哥哥们还笑我是不是变成牛犊子了,要在我鼻子上套个圈呢哈哈,多有意思啊母亲。
![]()
![]()
![]()
![]()
吱——刹车声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车已经开到了墓地前。坟前站满了来给母亲下葬的人。乌云密布,仿佛天上是一个世界,我脚底下的是另一个世界。我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等待着我的母亲。人群中传来:“轻一点,轻一点。”的叫喊声,七尺白布包裹的遗体递到了我们面前,我伸出双手,一只手从头一只手从腰把母亲的遗体接了过来,母亲的身体像是一个新生儿一样软绵绵地躺在我怀里。坟墓里格外的冷,我们像是把母亲绑在摇篮里一样,把她的遗体安放在了大地这片巨大的摇篮里。这一刻,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感觉到,她这是最后一次和我们,和这个世界道别。还是她只是以为这是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她的面容那么平静,和往常一样,仿佛这时我叫她:“妈妈。”她好像会回我:“哦,怎么了?”。围着墓地的人群把柱子搭在坑面,开始往坑里填土,我从柱子间看着母亲。随着土堆成型我能看到母亲的视野变得越来越小,只剩最后一点缝隙,透过这缝隙我看了母亲最后一眼,也是我与我那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最后一眼。
母亲离世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世界变得天昏地暗。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思来想去,往后余生,冬雪、春花、夏雨、秋黄,生者都活好了,才算是个有骨气的,像样的交代。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继续去爱那些已经逝去的人,我用我的方式,提笔写下关于母亲的记忆。
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母亲离开的事实,我们都知道死亡发生了,可它真正带来的关于“消亡”的意义,仍然让我悲痛万分。所以我宁愿母亲还活着,活在我的意识里,是的,母亲还活着,她活在我们的心里。我的母亲她伟大、平凡且勇敢,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她很爱自己的孩子们,对儿媳妇也是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宠爱,她一直以身作则教导我们端正做人,公正做事,致力于把孩子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总共怀了十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在五六岁的时候夭折了,还有一个在十三岁时不幸去世了。剩下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姐姐像是我们中间一朵娇弱的花朵,父母亲把最多的爱都给了姐姐,以前我还经常为此吃醋。不过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自然是家里的团宠。我在一个阿勒泰的一个小村庄出生,在这里长大。直到因为工作原因搬到了城里,自此便过去了二十年时光。父亲过世之后,母亲说要跟我一起生活,这一住,就是二十年,而就是这二十年成了我记忆里最难忘的时光。
![]()
母亲常年有疾病缠身,一直未断过服药,不过好在她可以自由进出,能自己独立吃饭。我的工作刚稳定下来,母亲就开心的像个孩子。我偶尔向广播电台、出版社投稿,母亲就变得很爱听广播,读报纸。她是我最忠诚的读者,期间从不错过我的作品,我回到家,她还会和我聊起:“孩子,今天有你的某篇文章,写得真好。”我也常把有发表自己作品的报纸、杂志带回家堆在母亲面前让她读,得到母亲的肯定我就把更多的作品投到出版社。每次被评为优秀,我就像个得奖的小学生一样把奖状带回家第一个给母亲看。我在宣传部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二十年我做过记者,也担任过领导工作,算是小有成就。这期间我也尝试着去接触摄影,在新的领域施展身手。母亲一直坚定地支持我,会认真看我拍的每张照片,不厌其烦地夸我:“拍得真好!”母亲在的时候,我的日子都是无忧无虑的。
最后十年,母亲因为上了年纪身体变得越来越弱,依靠药物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以前母亲是家里的智者、也是孩子们忠实的伙伴,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都会把孩子留给母亲照顾。孩子们也很喜欢自己的奶奶,有时候孩子们调皮犯了错,母亲就会护着他们不让我们惩罚孩子。孩子们也像是找到了避风港一样,会钻进他们奶奶的被窝里。他们会像朋友一样一起玩耍,甚至有时候母亲会因为跟孙子枪玩具而互相生气。这就是所说的人老了之后也相当于一个小孩吧。
类似这样的很多和母亲的记忆都留在了过去。我也无法靠言语讲述完母亲的一生。我会把与母亲的回忆当做护身符深记在心里。张枣有句诗写:只要想到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遗憾和心痛的瞬间会有很多很多,像细细密密的雪花埋在余生里,而现在我能做的,是好好爱着她生前爱着的人。爱着我,爱着哥哥姐姐们,爱着家里的孩子们,爱着延续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谨以此片献给母亲。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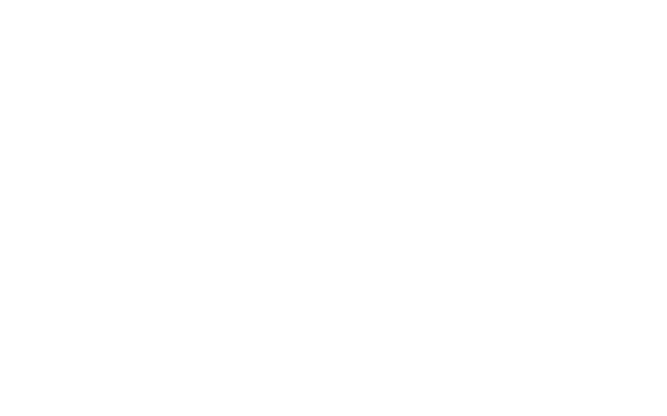

 2元
2元

 5元
5元

 10元
10元

 50元
50元





 举报
举报





 默认
默认 时光
时光 水墨
水墨 冬季
冬季 美好
美好 春节
春节 岁月
岁月 星空
星空 前行
前行 回忆
回忆









































